追象狂欢之外 “断鼻家族”的真实悲喜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和围观大象的新奇感比起来,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它们的家乡发生了什么、它们可以去到哪里,反倒没有激起多少关注和讨论。实际上,任何涉及种群的迁徙都是艰苦且危险的。如果不是有什么必须走的原因,它们不会贸然离开传统栖息地,踏上多年未有的漫长旅途。
记者| 吴淑斌 孙一丹
进城
当象群在前院调头时,王宏伟的视线正好与其中一头象对上。他直直地僵坐在一辆SUV车的驾驶座上,隔着前挡风玻璃,与大象短暂对视了两秒。如果大象想砸碎这块玻璃,他无处可逃。
王宏伟知道大象可能会来峨山县城。两三天前,他的朋友圈里就充斥着大象正在向城镇“进军”的消息。5月27日这天,早上7点多,社区工作人员还在微信群里发通知:“大象很有可能要往县城来,大家注意着点儿,晚上不要下楼。”虽然害怕,王宏伟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汽修厂——厂子就在玉溪市峨山县城的东北部,距离主城区只有100多米。前院还停着10辆崭新的小汽车,总价值在百万元以上。傍晚,员工纷纷下班后,王宏伟独自在店里守着,心里觉得“大象不至于到这儿来”。
厂子周围聚集着不少汽车修理厂,大多是一层的板房,每晚7点关门后,街上很快就不见什么人影了。王宏伟锁上前院的大门,坐在一辆新车里玩手机,晚上9点多,听见后院草丛窸窸窣窣,接着是树木被折断的咔嚓声。象群从汽修厂背后的高速公路护坡下来,撞破后院的铁丝护栏,闯入院子里。院内没有灯,但那晚的月光清亮,王宏伟看到几个庞大的影子越来越近,感受到地面传来的低频震动感。一头、两头、三头……三大三小,六头大象进到了后院。他挺直了背,不敢乱动,把手机揣进裤兜里,生怕屏幕的亮光吸引大象注意。象群似乎渴坏了,一口气喝光了后院大桶里存着洗车的2吨水,又走进前院。其中一头象与王宏伟四目相对。

6月6日,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拍摄的野象群(无人机拍摄)(新华社供图)
时间仿佛停住了。王宏伟看着大象,大象也看着他。他不记得僵持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全身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直到大象侧过身子,重新向后院走去。即使之前听说过“在大象面前不要跑动,躲藏起来”之类的警示,王宏伟下意识的反应仍然是“跑”。他拉开车门,飞快地冲出汽修厂,沿着马路狂奔,躲到了百米开外停着的一辆大型渣土车后边。那里停着几辆两米高的渣土车,用来拦住大象进入峨山县主城区的道路。
进入县城的大象有15头。它们来自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那里有著名的野象谷,是野生亚洲象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不过,游客想在天然环境中看到野象是需要运气的,野象平均每个月只会露面三四次,进入到城镇更是闻所未闻。这批离乡北上的象群由6头成年雌象、3头雄象、3头亚成体象和3头幼象组成,因为其中一头小象的鼻子曾经受伤,断了一截,被保护区里的监测员称为“断鼻家族”。2020年3月,“断鼻家族”就离开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到达峨山时,他们已经一路跋涉了400多公里。
大象迁徙原本是个正常现象。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告诉本刊记者,在西双版纳,象群常在不同保护区之间移动,1997年就有一个5头象的家族第一次从西双版纳迁到了普洱。后来,西双版纳的大象常有北移,但它们总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之间往返,没走很远。而“断鼻家族”的迁徙大大跨越了传统范围。去年10月份,它们走到普洱市中部的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时,就引起了郭贤明的注意——以前,只有独象走到过这么远。没想到,它们还继续北上,经过普洱、墨江县,并在途中生下一头象宝宝,数量增加至17头。随后,有两头大象结伴返回墨江,剩余15头大象继续北上。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摄影|刘飞越)
此前,象群行走在深山老林和周边的村庄之间,与人类保持着距离,直到2021年5月——出走一年零三个月后,它们抵达了玉溪市峨山县。峨山县是大象途径的第六个县,距离玉溪市区只有25公里,距离昆明市区不到100公里,全县常住人口大约有17万。进入这样人群密集的县城,在大象的迁徙路中还是第一次。
在王宏伟的汽修厂里晃荡近一个小时后,6头大象又上了街,与其他同伴汇合,排成一列,浩浩荡荡又慢速地朝着峨山县主城区的方向前进。马路上一片空旷,人们躲在街边楼上,用手机拍下大象在空旷的马路上漫步的视频。视频里,警笛声响起,大象缓步向前,来到四辆渣土车边上。躲在渣土车后的人群向后散开,尖叫声中夹杂着“好可爱”的惊呼声。为首的大象试图从车辆的空隙中钻过去,试了几回后放弃,带着象群回转身,上山离开了县城。随后一周时间里,它们加快了北上步伐,在6月2日进入昆明市晋宁区的边界。
阻截
自从大象在峨山“进城”后,一场人与象的拉锯战就开幕了。放任大象在城区到处游走,显然是不行的。郭贤明告诉本刊记者,象群越往北走、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对人和象都越不利。“大象不会完全按照人的要求来活动。我们这边的长期和象打交道,知道怎么应付,但玉溪和昆明远离传统的象群栖息地,那里的老百姓不知道野象的习性。”他担心,一旦人象冲突,既可能发生人员伤亡,也很可能对大象采取极端手段。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大象远离人群,想办法把象群引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政府每天投入四五百人力,进行无人机监测、预警通知、设置卡点、投喂食物、封锁象群靠近的村庄道路。但大象的前进方向飘忽不定,走到玉溪与昆明交界处时,象群曾一度折返玉溪,随后又连夜急行军转向昆明。亚洲象专家、现场指挥部、无人机小组,各种团队只能跟着大象的迁徙方向,随时变换地点。
5月31日一大早7点多,杨鸣金接到公司电话,让他“叫上几个司机,把六台挖掘机开到玉溪大河边上,去堵大象”。杨鸣金是玉溪一家挖掘机公司的小负责人,做河道清淤工作五六年了。四五天前,杨鸣金就从新闻上看到,大象已经走到了玉溪。但听到这个要求时,他还是有些发蒙,“怎么还要用挖掘机去堵?”

昆明市晋宁区料草坝村附近拉起了警戒线,有渣土车在此处“堵象”(摄影 | 刘飞越)
带着6台两米多高的挖掘机开到玉溪大河北边时,杨鸣金才明白,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堵大象”,而是为大象铺路。玉溪大河边人头攒动,警察、消防、渣土车司机、专家全都等在这里,象群正在紧挨着大河南面的草皮山上活动,已经在这里停滞了8个小时。
河道有3米多深,对象群里的幼象而言,下河后会陷在河道里难以上岸。杨鸣金的任务就是把河道两侧的土方垫高,挖出一个护坡,帮助小象下河后能重新上岸。河对面,沿着公路往东北方向再走10公里,就是玉溪市区。但如果往正北方向,就能进入人烟稀少的深山。河边通往玉溪城的玉洛路上,已经有74辆8米长、净重十几吨的渣土车挡在两端。一车又一车的菠萝、玉米、香蕉被运过来,铺在通往深山的路上,一共投放了4吨。“一边堵住大象进城的路,一边给它们开新的路,好吃好喝让它们乖乖地走呗。”杨鸣金这样总结大伙的工作。上午9点多,土方垫好后,6台挖掘机撤出了河道,加入阻截大象的渣土车队伍。
11点半,大象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草皮山的半山腰处,人群中一阵骚动,立刻被“嘘——”的声音制止。中午1点半,15头大象果然下山了,小象在前、大象在后,排成一列下到河里。此时,杨鸣金跟着人群被疏导到两公里外的地方,在这里,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劝返来往车辆。他后来听说,象群在河里洗澡、游泳,一直待到晚上11点,才踩着垫好的土方上岸,沿着设计好的“食物路”,边吃边爬上北边山坡。第二天,杨鸣金重新回到了大河边,发现路边玉米几乎被大象吃光了,菠萝倒是剩余不少。
这是象群第一次被成功“引导”。道路封锁和食物诱惑,可能是人类能对大象路线进行干涉的唯一方法。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一直在前方盯着,他告诉记者,此前工作组多次试图引导象群改变前进方向,都没有奏效。但这次成功的引导是否具有偶然性?陈明勇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会好好总结,在不激怒它们的情况下,柔性引导它们”。

大象进屋时,杨佳信就躲在身后这张小床底下(摄影|刘飞越)
虽然象群被引导着远离了玉溪城区,还是有人遭了罪。大象从玉溪大河上岸后,沿着山里公路不断逼近半山腰的一家疗养院,那里住着9名得过麻风病的老人,69岁的杨佳信已经住了40多年,因为麻风病,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右手几个手指头也缺了一截。6月1日下午5点多,大象排成一列,从这条人迹罕至的公路上山时,山下村庄的村干部打来电话,告诉他“大象来了,快上楼”。
很快,杨佳信就看到象群出现在门前空地上。他上不了楼,拄着拐杖迅速跳回房间,把门关上。慌乱中,杨佳信还试图用双手把窗户的铁栏杆掰断,翻出屋去。失败后,他缩进了里屋床底下狭小的空间里,拖来几个纸箱子挡在面前。在床下,杨佳信听到大象推开门,进到屋里打开水龙头喝水、吃苹果的声音,锅碗瓢盆被掀在地上,哐当直响。当看到一只象腿出现在里屋的地板时,趴在地上的杨佳信觉得,自己肯定活不成了。他掏出手机给唯一的亲人妹妹发了条短信:“门已推倒,我在床下。”幸好,里屋的门太小,大象挤不进来,停留了一会儿,转身穿过厨房,回到院子里。
“象进人退”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是否有人会受到攻击。无人机在随时监测着大象,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但郭贤明觉得,这算不上好办法。他曾经见过大象用鼻子卷起地上的树枝往空中抛,试图攻击紧紧跟随的无人机。“无人机和几百号人,每天跟着它,大象的心情可能特别狂躁,这样长期下去,可能会狂躁到崩溃。”陈明勇担心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便象群在远离西双版纳、普洱的区域找到合适栖息地定居,因难以与其他象群进行基因交流,出现近亲交配的情况,“这可能导致这个野象小种群的灭绝”。
为何离乡?
野象已经离开传统栖息地太久太远了,这是研究者的共识。而且,“断鼻家族”不是唯一出走的象群。2020年末,一个由17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小缺耳家族”,同样从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出发,向南迁徙,于今年2月和5月两次进入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自5月份进入以来滞留至今。
虽然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这些野象在城镇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爱又自在,但实际上,任何涉及种群的迁徙都是艰苦且危险的。最适宜亚洲象生存的,是海拔1000~1300米以下、有成片热带或亚热带森林的地区。海拔高、湿度大、坡度陡的地方,对亚洲象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这次“断鼻家族”路过的地方,有些位置的海拔已经超过2000米。如果不是有什么必须走的原因,它们不会贸然离开传统栖息地,踏上多年未有的漫长旅途。
郭贤明告诉本刊记者,保护区内植物种类的变化和大象种群的增长,是象群出走的主要原因。因为国家保护,禁止猎杀,近20年亚洲象种群数量在缓慢增长,目前整体分布区的数量大概在300头左右,“种群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自然扩散”。另一方面,保护区里“树长得越来越大,森林越来越密,不再适合草本植物的生长”,象能吃的林下植物在逐渐变少。
但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向本刊记者强调,只谈保护区内部的变化,是一种“避重就轻”。象群出走更大的问题,出在保护区之外的土地上。“大象的种群恢复与人类活动带来的栖息地减少,是此次象群出走的主要原因。从数据上看,虽然西双版纳栖息地的森林覆盖率在提高,但多出来的都是橡胶林,不适宜大象的生存。根据我们的统计,近20年里,西双版纳地区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减少了40.68%。”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1958年建立,1981年完成扩大范围、区划调整,保护区包含了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五个子保护区。五个子保护区在地域上互不相连,总面积大约24.25万公顷,占全州面积的12.68%,里面保留着较完整且集中的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
但是,保护区只是人为划定的范围,其实有将近一半的大象,活动轨迹在这12.68%的保护区之外。张立告诉本刊记者,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保护区外的很多农田都转换成了利润更高的橡胶林和茶园,“近20年时间里,西双版纳自然的乔木林、灌木林大概减少了1300多平方公里,保护区外边的种植园地增加了2700多平方公里,主要种植橡胶、茶叶,而这些是从乔木林、灌木林、疏林地甚至农田转化过来的”。
“它们走得很快,我推测有几个原因。首先,栖息地质量下降,食物比较少,是象群持续北上的重要原因。普洱的森林质量比较差,以思茅松、西南桦为主,大象可取食的食物只有40多种。出了普洱越往北走,比如玉溪、昆明的林地质量就更差,没有什么可取食的东西,所以大象更依赖于老百姓的庄稼。然而,现在正值旱季,田里也没什么庄稼,大象要加速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
苏朴怀是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内关坪村的彝族人,今年68岁。他告诉本刊记者,30多年前,种地是没什么人管的,还可以把森林砍了,开成农田,那块地就成了自家的。那时候口粮紧,一亩地的稻谷够全家人吃上一年,苏朴怀和许多村民一样,把自己的10亩地全都种上玉米和稻谷。恼人的是,这些作物正好都是象爱吃的东西,大象的频繁侵扰让他们愤怒而无奈。传统的火炮枪早就不让用了,大象也不怕鞭炮、火把之类的东西,农民只能扯一块篷布盖住庄稼,任由大象在田里吃饱后离开。最多的时候,苏朴怀家里被大象吃掉、踩烂的农田面积能达到5分地。“一亩稻谷,国家只赔个四五百块钱,够买多少米?”
1995年,苏朴怀发现,橡胶的价格大约在18块钱一公斤,接近水稻价格的6倍。橡胶喜欢高温、多雨、肥沃土壤的地方,非常适合西双版纳。苏朴怀算了一笔账,虽然橡胶树的种植周期长,种下后需要等8年才能成熟割胶,但一棵树能割二三十年,每年至少可以割下180多斤胶,算下来,一年的利润是稻谷的五六倍。而且,橡胶树是大象吃不掉的东西,只要把树下的草除干净,就不容易招引大象了。他从农田的边缘开始,慢慢往中心种橡胶树,如今10亩地里有6亩已经改成了橡胶林。靠着不断扩大的橡胶种植,苏朴怀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景区附近张罗起一家规模不小的餐馆。

玉溪市峨山县玉林村,象群吃光一片玉米地,还把大棚损坏了 (摄影|刘飞越)
村民找到了能够防御大象的“致富作物”,如今,橡胶林已经成为保护区周围农民种植最多的作物。驾车从西双版纳的市区景洪一路向北或向南,公路依着山势沿澜沧江在一片绿色的林中蜿蜒,路两旁的山坡上,全是如同士兵一般排列整齐的橡胶林。中国科学院学者曾对西双版纳橡胶林面积进行遥感监测,发现1990年至2010年是橡胶林面积增长最快的20年,每10年的增幅都超过50%。6月份是割胶时间,保护区周围的村子几乎空了,青壮年上山割胶,一天能割下两三百块钱。
虽然看起来也是森林,但橡胶林中的生态多样性大打折扣,被称为“绿色沙漠”。2011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修订了关于天然橡胶的管理条例,禁止在国有林、集体林中的自然保护区和水源林、国防林、风景林地、基本农田地、旅游景区、景点与海拔950米以上和坡度大于25°的地带开发种植橡胶,坡度大于25°的分水岭、沟谷坡面和橡胶林地,应当逐步退胶还林、退耕还林。
不过,这并没有给苏朴怀带来太大的困扰,他原本也不打算扩大橡胶林了。这几年,橡胶的价格不断回落,茶叶的价格倒是上涨了不少,苏朴怀开始合计着,多把一些地种上普洱茶和古树茶,依然是大象不爱吃的植物,或许收入还更可观些。
“一面是当地的经济发展,一面是亚洲象栖息地的逐步丧失,二者很难找到一个平衡。”张立说,由于栖息地的破碎化,增大了亚洲象生存压力,最终迫使一些个体走出保护区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次北上的象群便是其中之一”。
城市想象
从峨山县城离开后,象群翻过一座山,进入了山背面的玉林村。夜里9点,住在村庄北部的林祥伟带着家人上到三楼的天台,看着四头大象在屋前的玉米地里饱餐之后,慢慢悠悠地朝着自家院子走来。起初,林祥伟担心自家养的狗“小黄”惹怒大象——“小黄”上个月刚下了四只小崽,护犊心切,听到大象啃食玉米的动静时,就已经狂吠一阵。但大象真正进到院子后,“小黄”乖乖地趴在笼子里,看着四个庞然大物来回走动,一声不吭。
一头大象用鼻子钩住挂在院子里的鸟笼,摔到地上,随后一脚踩坏了笼子。幸好,笼子砸到地面时,门被震开,里头的黑色八哥滚出来才保住一命。直到凌晨2点,大象已经离开了4个小时,林祥伟下楼收拾残局时才发现,平时吵吵闹闹的八哥仍然躺在地上,像受了惊吓还没回过神,不叫唤,也没有飞走。
象群轻而易举撞开铁门的画面让林祥伟大为震惊。他的心跳得很快,怕大象伤害到家里人,又对眼前庞然大物表现出的温和感到惊讶。大象在林祥伟的院子里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除了踩碎鸟笼、吓坏八哥,还撞坏一扇卫生间的门,没有给家里带来别的损失。一直到大象返回山上,他听着象群在山林里不断发出的嘶吼声,仍无法入睡。最兴奋的还是3岁的女儿,大象走后的几天里,她反复追问林祥伟,“大象的家在哪里?大象为什么要来我们家呀?它们还会再来吗?”

6月5日,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无人机侦察小组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利用无人机监测象群方位,吸引村民围观 (图 | )
象群北迁的过程中,网上不少文章和视频都在展示着亚洲象的可爱,用逛街、吃货、自由行来形容它们的行径。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情节是,象群经过峨山县大维堵村时,一头小象因为闯入一户开酒坊的村民家里,偷吃了200斤酒糟,醉倒在田间而脱离了大部队,醒来以后“四处游玩,不亦乐乎”。
然而,本刊记者实地走访故事里提到的村庄和村民后,最终确定并没有发生小象醉倒的事情。不过,的确有14头大象造访了小酒坊,共吃掉100斤酒糟和1600斤粮食。“小象的食量没那么大。一头成年象吃掉200斤东西需要一天时间,象也不太可能喜欢酒糟的味道。”郭贤明对本刊记者说,“我看到有新闻说小象吃了200斤酒糟,就知道一定是假消息。”但这个类似童话的情节,至今仍在网上流传。
但实际上,在专家眼里,出了普洱越往北走,比如玉溪、昆明的林地质量就更差,没有什么可取食的东西,所以大象不得不走入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人们的密集围观和驱赶,可能让大象受到惊吓,象群的应激激素,也就是荷尔蒙的皮质醇水平会增高。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下的象群,并没有城里人想象的那么可爱,而是有危险的,那些多年和它们相处的村民知道厉害。
“外面的人都不怕大象了。”看到网上对北迁象群的追捧和萌化,苏朴怀觉得有些好笑,也无法理解。他的家距离野象谷只有5公里,和成片的原始森林也只隔了一条马路。苏朴怀和野象打了50多年的交道,对他而言,野象是像小猫小狗一样熟悉的动物,但又觉得“很讨厌,烦得很,一点都不可爱”。他们的庄稼地就在山里,紧挨着森林,常常有亚洲象从森林下到农田里,吃苞谷、稻米,当地村民不堪其扰。

2017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门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在芭蕉地查看被野象损毁的情况,他们根据留下的痕迹分析象群的情况。(图|视觉中国 刘冉阳 摄/中新社)
20多年前,火炮枪还被允许使用,苏朴怀就和村里人相约背着枪上山种地。遇到大象来吃庄稼时,人排成一行,往大象身旁放空枪,“呵(吓)跑它们”。吓不跑的,村民会往大象的腿上开枪,打疼了,大象就跑了。后来,枪支不让用了,村民们开始在田埂上烧火、放鞭炮。这些方法在最初几年还能奏效,但聪明的大象很快就习惯了这些“虚张声势的玩意儿”,隔着火堆,也敢大摇大摆地吃苞谷。
到了2000年左右,枪支被禁,大象也被国家法律保护起来,村民在与象的对抗中成为“弱者”:“打死了大象要坐牢,大象踩死你,只会赔一笔钱。”苏朴怀知道的最惨烈的一次事故发生在2019年,同乡村民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正面遇到大象,从摩托车上被撞倒在地。象鼻卷起村民甩动了三四圈后,人就没气了。
几十年来,村民们积累了许多“躲象”经验,包括大象身上的臭味能传出一公里远,上山种地要晚出早归,避开大象活动频繁的凌晨、傍晚和深夜等。看到我们开车在野象谷附近晃荡,苏朴怀很认真地提醒,不要穿白色的衣服,大象最反感的就是白色、黄色、红色。绿色和灰色衣服是最好的,遇到大象时,只要一转身躲进大树后面,象就找不着了——但爬上树是大忌,如果大象愿意,撞倒一棵树轻而易举。开着汽车遇到大象时,要赶紧把车横在象的面前,弃车跑进树林里躲藏。他看了许多抖音视频,对外地人对野象的追逐感到不解,“外面的人居然都不怕它们”。
“网红”
围观大象,正在成为一场网上的狂欢。
自从在峨山县“进城”后,“断鼻家族”迅速成为彻头彻尾的网红,许多人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云追象”,看看大象走到了哪里。在象群造访过的村庄,大象更是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村民们不吝于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者讲述大象进村的事情。
当本刊记者沿着大象走过的路线,进入许多一度被封锁的村子时,往往只需要拉住一位老乡问“见到大象了吗”,就能迅速拉近双方的距离。对方的话匣子马上打开,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也会热情地引你到目击者那里去。很快,就会有其他村民围过来,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组成一场情绪高涨的“大象进村追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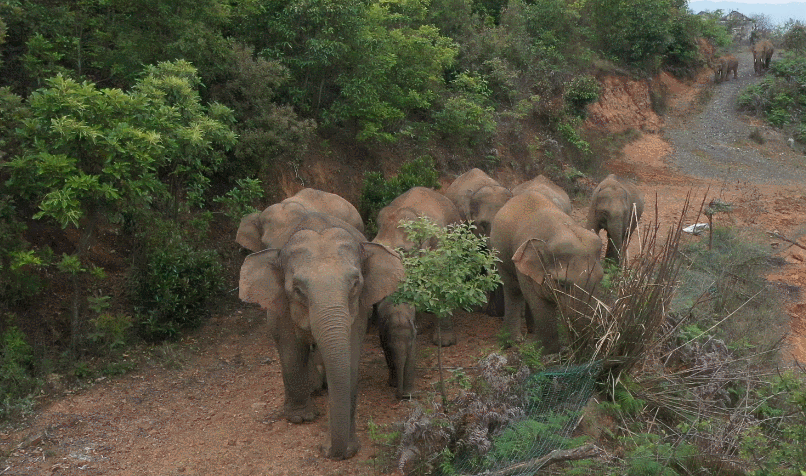
6月3日,大象出现在昆明市晋宁区料草坝村的山沟附近,随后继续向北迁徙。第二天,料草坝村旁的马路上仍拉着警戒线,有四名警察值守,对每一辆进入的车辆仔细询问,非本村村民不能进入。人群三三两两地在路边聊天,许多附近的村民骑着摩托车赶来守着,甚至有不少人驱车五六十公里而来,只希望有机会亲眼看到野象。
警戒线外的记者常常能精准地认出同行。全国各地的媒体不断聚集到玉溪,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数量达到了顶峰,已经超过了20家。监测大象的现场指挥部一般设置在附近村庄的村委会里,起初,指挥部还对媒体开放,记者可以进到指挥部,观看无人机传回的航拍画面和红外线追踪情况。但媒体越来越多,指挥部干脆移到了警戒范围内,再也不让轻易进入,只是每天发出几张更新的图片和文字。为了独家拍到大象的一手影像资料,开车寻找野路、翻山进村、深夜闯关,都是被尝试过的方法。
网络主播自然不会缺席观象活动。在料草坝村,一位30多岁、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主播晓雯无法进入封锁的村子里,只能把镜头在周围来回扫动,拍一拍围观人群和执勤工作人员,最后对着远处的山林和农田,向观众解释:“这是大象曾经走过的山和玉米地,大象还在附近哦。”晓雯告诉本刊记者,这是她第二天到这里,来得晚,已经错过封锁不严格的最佳时间,拍不到什么好的画面了,“但这么大的事情,总得参与一下”。她口中来得早的主播,曾因为在玉溪大河边直播吃象群剩下的菠萝,招来一片骂声。

和围观大象的新奇感比起来,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它们的家乡发生了什么、它们可以去到哪里,反倒没有激起多少关注和讨论。“断鼻家族”像一群闯入人类世界的大型宠物,真实的悲喜不为人知。如何引导象群去往适合它们的地方,或者引导它们往南返回传统保护区,如今还没有专家给出具体方案。即使已经研究亚洲象30多年,郭贤明也感到无奈,“我从没做过这样的方案,也没听说过有这种方案”。
目前,“断鼻家族”还游走在昆明和玉溪的界线上。6月15日, 象群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活动,其中一头公象已离群10天,与象群直线距离19.1公里,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林地内活动。越往北,人口越密集,林地质量越差,它们能在野地里找到的食物就越少,与人类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它们只能不断往前,行走是它们不得不做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文中杨鸣金、晓雯、苏朴怀为化名,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25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责任编辑:张亚楠
本文由今日都市网发布,不代表某某资讯网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
